搶奪品質外賣紅利、門店模型矩陣式發展,品牌衛星店迎爆發期
李春婷 · 2024-05-31 14:06:49 來源:筷玩思維
從去年末到現在,餐飲界討論最熱門的店型恐怕要屬品牌衛星店了。
據筷玩思維前線記者在各城市商圈調研時發現,必勝客、肯德基、老鄉雞、醉得意、農耕記、海底撈、木屋燒烤、茶顏悅色、冰火樓等均在嘗試品牌“衛星店”的新模式。
品牌餐飲在自身門店周圍拓展出多個小型外賣店,在價格方面與堂食門店相比,有明顯下調。連鎖餐飲品牌們紛紛布局衛星店,看中的是大店打品牌、小店提利潤的雙模式驅動效應。
這種模式逐漸在餐飲大品牌之間形成一種低調的默契,不少大品牌扎堆在臨街社區、餐飲外賣共享廚房以及大型寫字樓的負一層美食城開出小店(主要為后廚場地),悶聲賺大錢。
不是說純外賣店沒有機會嗎?為什么這些大牌卻反其道而行、開出許多這種專門做外賣的“分身店”、衛星店呢?
說白了,用戶點外賣的需求已經很大,外賣店如何應對和滿足這種需求?這才是思考的著力點,而并非單純的考慮“純外賣”還是非純外賣。
那么,是否所有品牌都可以做衛星店?這就要弄清楚品牌衛星店的底層邏輯了,思維決定行動的正確性,一味跟風則難免出現問題。

衛星店模式適合有堅實的主力店根基和品牌力的餐企
衛星店的基本邏輯是什么?這個概念大約首先來自汽車銷售。汽車生產廠家在市里邊設置4S店,即中心店,職能是銷售產品、展示形象,并為其它“衛星店”提供物流配送、技術以及售后等服務。
衛星店則與中心店相配合,負責銷售、維護,直接服務于一線消費者,為離4S店比較遠的消費者提供便利。
這個模式后來被餐飲業引用,餐飲類衛星店也大多被稱作品牌衛星店,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一種認同:餐飲業的衛星店離不開品牌根基。
同時,對應過去品牌主力門店的堂食和外賣混合經營模式,品牌衛星店不再提供傳統的堂食服務,專注于提供高性價比的品質外賣。
有圈內人士直言,堂食和外賣分離將是所有正餐、休閑餐飲等以線下體驗為主的餐飲的大趨勢。
品牌衛星店的店鋪通常面積更小,位于外賣高客流區域,人力及房租成本低,回本周期快,能快速、高效擴大市場覆蓋、增加品牌曝光度,并貼近當下消費者用餐需求。

說起大牌餐飲做衛星店,我們首先來看看海底撈。從2023年7月開始,海底撈推出一人食“下飯火鍋菜”并上線外賣專營店。海底撈•下飯火鍋菜就是一個典型的衛星店模型。
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衛星店的特點:店型面積小,選址靈活,快速布局占據市場點位;借助外賣或自提方式輻射全域客流,分散在主力門店周圍來專門覆蓋高頻剛需的外賣用戶;基于綜合成本的降低,使得產品價格優勢凸顯。
這種面積大概十幾平米,月租金大概只有1到2萬元,相對于大品牌餐飲的堂食門店來說,成本可能僅僅只占了其中十幾分之一,但單店營收每月可以達到20到30萬甚至更多,總利潤并不比堂食店低。這一結果的取得離不開衛星店的品牌效應,這也是品牌衛星店最主要的底層邏輯:繼承母品牌資產,消費者天然信任,可快速增強品牌力,同時還能將品牌效應的影響最大化,從品牌的角度來說,就是雙向獲益。
相比較而言,對于品牌力一般甚至是初創品牌,普通的門店還不具備品牌勢能,顯然是不適合開品牌衛星店的,否則就成了外賣發展史上一度火爆卻很快被拋棄的“純外賣店”模式。

品牌衛星店基本選址在熱門商圈冷門位置,投資少、回本周期短
除了要具備相當的品牌根基,品牌衛星店模式成立的另一個關鍵在于選址。能否在合適的位置選擇衛星點位,這決定了“衛星”在圍繞主力店正常運轉的同時,能否做到低成本獲取高流量。
例如,長沙本土湘菜品牌“冰火樓”開出的“冰火樓外膳”,也是被業內津津樂道的衛星店經典案例。地處非一線城市,冰火樓在當地的品牌效應自不必說,但衛星店仍然選擇了長沙五一商圈,而并非不知名的冷門區域。
于是才有了冰火樓的衛星店在開業僅4天、沒有做過任何宣發的情況下就“爆單”的新聞。“外膳”符合衛星店的基本要素:店型面積僅約50平米,沒有堂食,專營外賣,人均客單價50元,卻能做到單店月營收30萬。
類似的外膳微型衛星店目前已有18家門店,遍布長沙市人流量集中的核心地段,選址則都位于社區餐飲區、熱門寫字樓底商等冷門位置。之所以這樣選址,就是為了一方面占據點位,一方面降低租金這一成本大頭,實現低成本布點、快速回本。一般來說,運營良好的品牌衛星店的回本周期可以低至半年左右。
打造品牌衛星店,一定程度上是疫情常態化下的產物。品牌面對堂食客流的不穩定,加之開店成本大、風險高,轉而以純外賣店來解決觸達外賣高頻用戶的問題。
而在當下,這種模式愈發適應市場對外賣需求持續增長的大環境、成為了備受青睞的商業模式。

依然是在長沙,即使每隔50米就有一家的茶顏悅色,也搞出了“茶顏外賣鏢局”的衛星店,在疫情期間,由于不支持外賣,茶顏悅色門店出現的“黃牛”代購跑腿費就高達100元,于是才有了自營配送的“鏢局店”。
后續茶顏悅色也持續開出專營外賣的衛星“鏢局店”,位置也是在熱門商圈冷門位置,以至于有些想要去店里自提的顧客,在高德地圖上都找不到門店位置。
還有一些品牌餐飲直接選擇了入駐品牌化的共享廚房,以此來更加快速、低成本地開設自己的衛星店,農耕記的一些衛星店直接入駐了位置更好、單店體量更小的星選閃電廚房,熊貓星廚共享廚房也有不少入駐商家是品牌餐飲衛星店。
這種模式也恰好契合了“外賣騎手可接近性”的需求,因為共享廚房往往是騎手最容易識別的位置,多個騎手在用餐高峰期集中配送,這可以大大提高附近5公里的配送力,而現在像美團、餓了么這樣的平臺也會為新商家提供AI選址的服務,就是基于這個邏輯。

無論如何,要想實現衛星店的極致成本控制,選址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,這也是從規模上和主力門店相區別開來,獲得和主力門店完全不同需求的那部分顧客,盡可能地覆蓋全域客流。
無堂食、更少的SKU,衛星店從根本上解決了快慢沖突問題
事實上,外賣這一餐飲經營零售化的經典模式,一直都在不斷迭代。有市場洞見的品牌餐飲人從沒有放棄過外賣,因為他們早就知道,外賣與堂食的邏輯不同,外賣解決吃飯剛需,注重極致效率和便利性,講究的是“快”,而堂食解決線下體驗,注重顧客的社交需求,講究“慢”的舒適性,“快”、“慢”兩條不一致的邏輯如果放在一個門店里,必然要打架。
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在門店經營時間、動線規劃和產品結構區分上,往往不能二者兼顧,以堂食起家的商家顧此失彼,只好先保證堂食模型的正常運轉,有的甚至徹底放棄外賣業務。
這種逃避的態度必然不能長遠,一些品牌在疫情倒逼下重新梳理出外賣的邏輯,這也是現在品牌衛星店能夠突然形成小風口的原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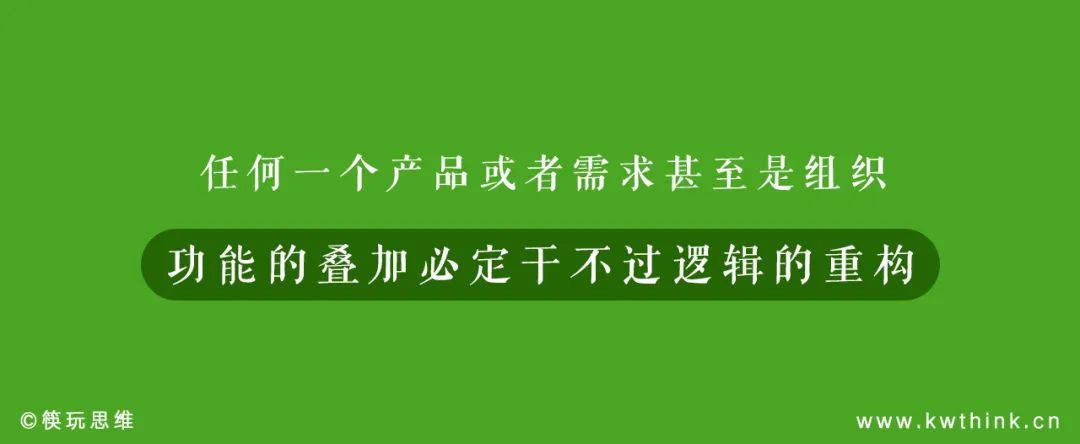
眼下,衛星店從根本上解決了快慢沖突,不再寄生于堂食,不再受累于“堂食+外賣”雙主場運營,堂食店不再期望靠外賣來釋放更多單店效能,以此徹底實現餐飲零售化的商業模型。
在這樣的模型下,除了房租成本低,整體運營輕量化同樣重要。一旦剝離堂食的束縛,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精簡SKU、滿足更符合一人食用餐需求以及打造更具價格吸引力的新菜單。
海底撈“下飯火鍋菜”就直接把菜單改造為冒菜,有和牛冒菜、滑牛午餐肉冒菜、豆花冒菜、七只蝴蝶蝦冒菜等10款“冒菜+飯”的組合套餐,消費者還可以自己選擇湯底口味和制作方式,如燙菜和干拌兩種形式,套餐產品價格在30到40元之間。
但菜單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論,還是要結合主品牌門店本身的品類特點來調整。
像冰火樓外膳店這樣的衛星店,則做的是現炒現做的模式,SKU高達30多個,菜品也以家常菜為主,且和堂食店菜品重復度不高。

其實,西貝的首家外賣專門店早在2017年就已經開出。不過后來,西貝并沒有持續做這種早期的外賣衛星店,而是在“品質外賣”上下功夫,把精力放在研發適合外賣的套餐以及配套的包裝、附加服務等。
本質上其實還是符合了餐飲零售化的邏輯,只不過西貝的門店分布廣,外賣業務剝離出來得比較早,已經有了自己的一套產品架構和動線管理,也就沒有迫切開拓品牌衛星店的動力。
然而,本質上“品質外賣”就是在探索獨立化的外賣體系,理順餐飲零售化與堂食店體系的關系,最終的結果是積極的。去年12月22日,西貝方面表示,其2023年外賣業務營收將超過20億元,同比增長25%,訂單量同比增長35.5%。

結語
仔細回顧可以發現,品牌衛星店的勢頭早就在醞釀,即使門店遍布全國的百勝中國,也在2022年就提出旗下必勝客、肯德基品牌都在嘗試“衛星店”的小店模式,采用“一托多”、“子母店”來縮短開店回報周期、加密商圈的門店密度、擴大外送覆蓋范圍半徑,從而提升在外賣市場的份額。
百勝中國CEO屈翠容曾表示,必勝客在2022年新開門店中約有5%是小店或者“衛星店”,而這一類型門店在肯德基新開門店中占比約有50%。
其實外賣專營店早已不是新鮮事物,甚至已經完整經歷過了探索期、走紅期和衰落期,為什么專門去做外賣業務的“品牌衛星店”卻在此時“橫空出世”,乃至有望成為2024年的店型之王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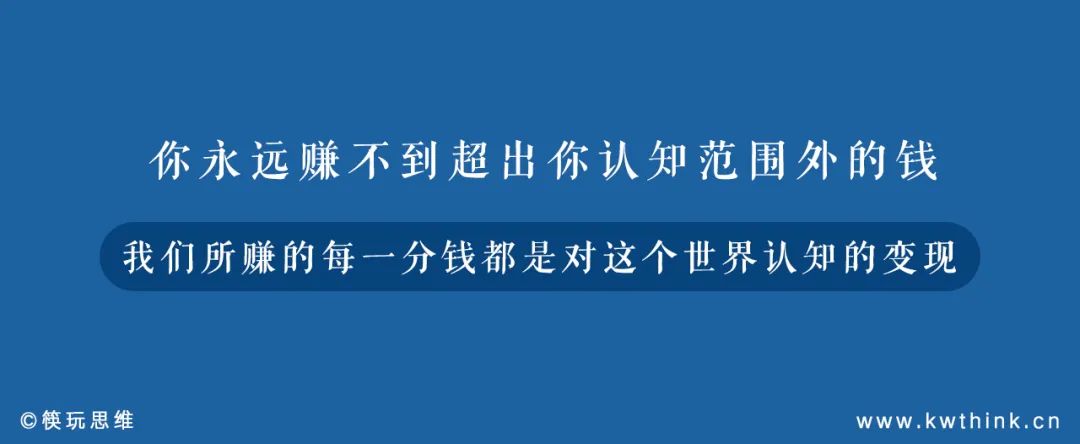
想必文章至此,大家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。而在筷玩思維看來,無論是已經All in這種模型、持續探索門店模型矩陣式發展的知名品牌餐飲,還是在觀望中的普通餐飲企業,大家都需要重新思考的是:外賣這一形式應當如何做到和自身高度適配、放大品牌勢能、擴大客群和提升復購率。
畢竟,外賣是餐飲零售化分支的核心部分,必然要擁抱而不是放棄,大眾消費者也越來越“精明”和理智,“低價吃大牌”、“無限追求質價比”將是商家必然要順應的消費主流。
越來越多的正餐大品牌發力衛星店也加速催生了“正餐快餐化”趨勢,在這一趨勢下,讓原本主營快餐的品牌更難受了,快餐品牌的市場空間被進一步蠶食。
本文轉自自筷玩思維;記者:李春婷
熱門文章
- 1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寫評論
0 條評論